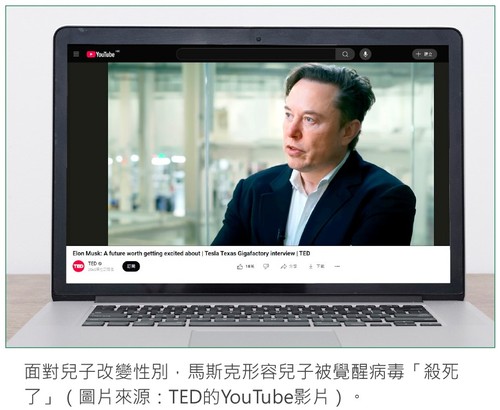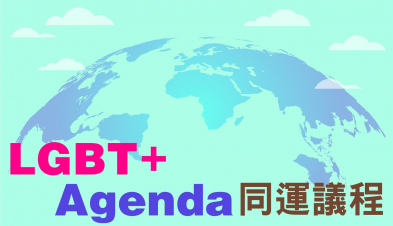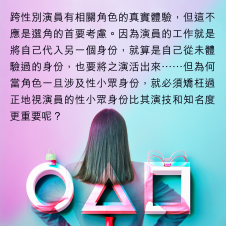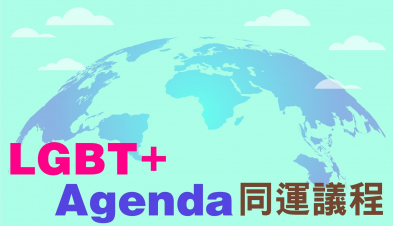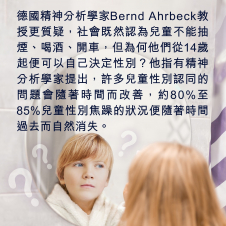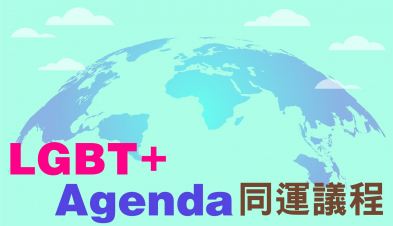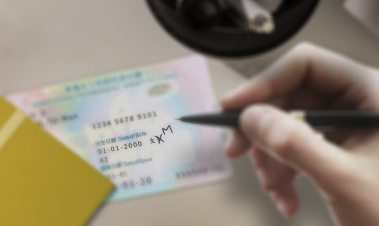同性婚姻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1]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2] 泰王哇集拉隆功在2024年9月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有關法律已在2025年1月23日生效。[3]
來自南韓的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了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4]
信仰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當中列明不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不過如是Fuller神學院的高級員工來說,他們則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Schmidt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5]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5月2日,大會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這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相關的剩餘禁令。[6]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是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2024年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由於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曾有逾萬人在網上平台簽名,要求撤換這幅畫作。[7]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表示教會應該歡迎跨性別者,而不應該歡迎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梵蒂岡又拒絕「性別理論」,因為它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這是梵蒂岡不接受的;另一種則因為「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尋求醫療方面的協會,梵蒂岡是會接受的。[8]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進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9]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最後獲得58,000英鎊的賠償。[10]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於是他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校區及教育局亦承認Bloch的言論沒有違反州政府的政策,他的行為不涉及騷擾、捉弄和欺凌。[11]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2]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Phillips提出訴訟。[13]
性別肯定治療
從2024年1月開始,美國阿拉巴馬州及路易斯安那州開始實施法例,禁止醫療人員為18或19歲以下未成年人士,提供跨性別治療,當中涉及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或進行性別重置手術。[14] 到了8月,俄亥俄州及佛羅里達州亦實施了類似的法例,禁止為未成年人提供相關的跨性別治療。[15]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公佈了新修訂《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內容,法案原本禁止在聯邦資助的學校出現基於性別的歧視及騷擾行為,新修訂內容將有關定義擴展至禁止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懷孕或相關情況、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特徵作出歧視行為。[16] 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7]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8]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育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由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19] 英政府在2024年5月時頒佈臨時禁令,宣佈在6月3日至9月3日禁止私營處方者向未成年人士處方青春期阻斷劑,[20] 到了12月,英政府再宣佈,將無限期禁止向未成人提供或銷售青春期阻斷劑的禁令,並會在2027年檢視有關政策。[21]
涉及運動項目的爭議
2024年4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愛達荷州可實施法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或手術等性別肯定治療。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不但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肯定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22]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23]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24] 但在6月24日,縣政府的立法機構通過了類似的禁令,有關法令禁止有跨性別成員的女子運動隊伍使用縣政府提供的運動設施,法令已在7月15日獲縣長簽署及生效,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則在當天再次入稟法院,指控禁令觸犯了紐約州的反歧視法。[25]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26]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27]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28]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29]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30]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體育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31]
涉及更改性別標記與稱謂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認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實屬違憲,有關法令不符合政府的利益,更讓跨性別者因要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而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法院駁回了案件,提訴人為此上訴,2024年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32]
在美國,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掌的州份在2023年相繼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33]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維珍尼亞分部在2024年2月對維珍尼亞州的教育部門提出兩項訴訟,要求法院推翻相關針對跨性別學生的政策,有關政策允許教師及學生依照跨性別學生出生時的姓名及代名詞來稱呼他們。不過,其中一宗訴訟在7月時已遭約克縣的巡迴法院駁回。[34]
2024年11月1日,德國正式實施《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35]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36]
與性別議題相關的立法或裁決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在蘇格蘭正式生效,該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罪行。新增的條文會加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37]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的人士收養俄羅斯兒童。法案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38]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人士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法定要求提出訴訟,訴訟期間原訴人曾透過律師指,手術要求令其經濟和身體帶來巨大負擔,並認為要求違反了憲法保障的權利。日本最高法院在2023年10月裁定有關法定要求違憲,並將案件發回高等法院審理。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在不接受變性手術的情況下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39]
[6] Joey Butler, “May 3 wrap-up: Historic conference comes to a close.” UM News. May 3, 2024, https://www.umnews.org/en/news/may-3-wrap-up-historic-conference-comes-to-a-close; Rev. Joelle Henneman, “On toward Christian perfection after General Conference.” UM News, May 24, 2024. https://www.umnews.org/en/news/on-toward-christian-perfection-after-general-conference; Heather Hahn, “United Methodists remove same-sex wedding ban.” UM News. May 3, 2024. https://www.umnews.org/en/news/united-methodists-remove-same-sex-wedding-ban; Heather Hahn, “Church ends 52-year-old anti-gay stance.” UM News. May 2, 2024. https://www.umnews.org/en/news/church-ends-52-year-old-anti-gay-stance; Heather Hahn, “40-year ban on gay clergy struck down.” UM News. May 1, 2024. https://www.umnews.org/en/news/40-year-ban-on-gay-clergy-struck-down;〈聯合衛理公會大比數通過決議 修訂婚姻定義刪五十載反同條文〉,《時代論壇》,2024年5月14日,網站: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4427&Pid=102&Version=0&Cid=2143&Charset=big5_hkscs&fbclid=IwY2xjawCyr-hleHRuA2FlbQIxMQABHYCLbPO1JIL4uYZT3nzDUtMXx4wakr1iavqZqwp9JBb3OZHOUmG5tFcarQ_aem_AXorFuV3DHKOdCuLpeHMTE1u076W-Fl1pMdRZebcUUQMrmfxESYjErliX7r-bcKTMLm2Tg6XxvZlJvN2XvoYHYdJ。
[7] Ciarán Giles, “Too pretty? Easter poster depicting a handsome, fresh-faced Jesus prompts criticism in Spain,” AP,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spain-easter-poster-salustiano-jesus-e09de88385f8f50fea5f6260b0b35a5d; “'Sexualised' Jesus painting sparks controversy in Spain,” BBC News, last modified February 6, 2024,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240205-sexualised-jesus-painting-sparks-controversy-in-spain.
[21]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Ban on puberty blockers to be made indefinite on experts’ advice,” GOV.UK,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1, 202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an-on-puberty-blockers-to-be-made-indefinite-on-experts-advice; Gabriela Galvin, “The UK is the latest country to ban puberty blockers for trans kids. Why is Europe restricting them?,” Euro News,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3, 2024, https://www.euronews.com/health/2024/12/13/the-uk-is-the-latest-country-to-ban-puberty-blockers-for-trans-kids-why-is-europe-restrict.
[24] The Associated Press, “After a county restricted trans women in sports, a roller derby league said, 'No way'.” NBC News. March 28, 2024.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politics-and-policy/county-restricted-trans-women-sports-roller-derby-league-said-no-way-rcna145444; Parker Schug, “Nassau County's transgender athlete ban struck down in county supreme court,” LI Herald.com, May 13, 2024, https://www.liherald.com/stories/blakeman-faces-more-legal-pushback-on-executive-order,207782?.
[25] Claire Fahy, “County Legislature in N.Y. Suburbs Passes Transgender Athlete Ba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24/nyregion/transgender-athlete-ban-nassau-county-ny.html;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news/new-york-county-passes-law-restrict-trans-girls-women-sports-venues-rcna158786; https://abc7ny.com/post/long-island-new-york-politics-nassau-county-legislature/15060816/; Jo Yurcaba, “New York county's transgender sports ban takes effect,” NBC NEWS, July 16, 2024,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news/new-york-countys-transgender-sports-ban-takes-effect-rcna161949.
[35] “German upper house passes gender self-identification law,” DPA,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May 17, 2024, https://www.yahoo.com/news/german-upper-house-passes-gender-130018509.html; 〈德國「性別自決」法案生效 一年可「變性」一次〉,星島頭條,2024年11月3日,網站: 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world/3397923/%E5%BE%B7%E5%9C%8B%E6%80%A7%E5%88%A5%E8%87%AA%E6%B1%BA%E6%B3%95%E6%A1%88%E7%94%9F%E6%95%88-%E4%B8%80%E5%B9%B4%E5%8F%AF%E8%AE%8A%E6%80%A7%E4%B8%80%E6%AC%A1; Steven Paulikas and Zana Çobanoğlu, “Self-Determination Act Creates New Rights for Transgender People in Germany,” American-German Institute, June 24, 2024, https://americangerman.institute/2024/06/self-determination-act-creates-new-rights-for-transgender-people-in-germany/; “Declarations under the Self-Determination Act,” German Miss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ccessed November 28, 2024, https://uk.diplo.de/uk-en/02/naming-law/declarations-under-the-self-determination-act/268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