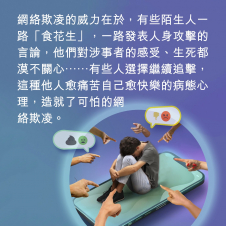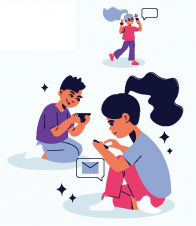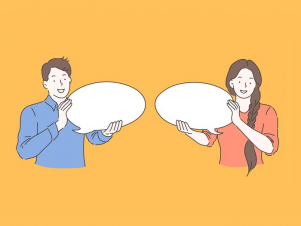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 除了第一層次的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另外還有第二層次的數碼創作(Digital Creativity)及第三層次的數碼創業(Digital Entrepreneu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