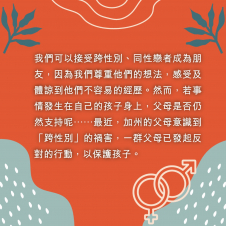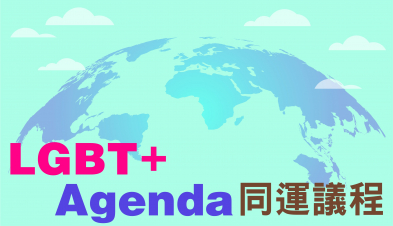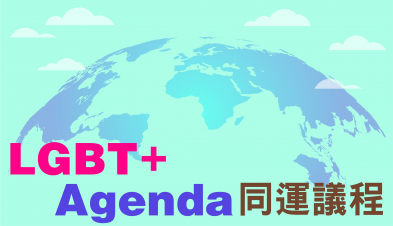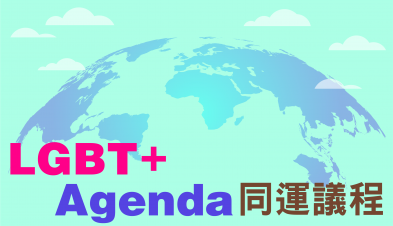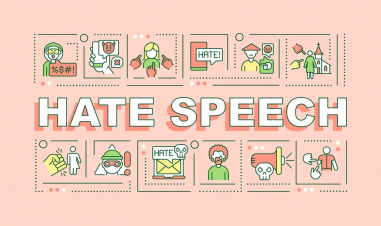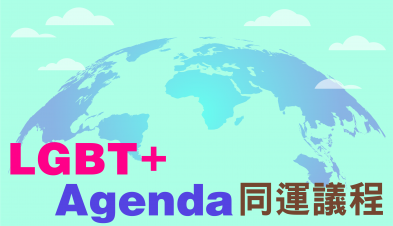同性戀是一個複雜又專業的課題,當中包括生理結構、心理學、臨床醫學和倫理學等學術範疇,同時觸及婚姻及家庭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政策、醫療專業、人倫、宗教和傳統風俗的價值觀等層面。「同性戀」一詞在全球性解放思潮中被高度政治化,是一場「性/別」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政治壓力下,如果在討論同性戀議題時,不採取「肯定同性戀向導」(gay affirmative approach)就是「政治不正確」,即時被歸邊受敵,淪為歧視弱勢的霸權、沒有愛心的審判者。
《認.同──關心同性戀(第二版)》小冊子是一本工具書,透過綜合一些學術研究、調查數據、真實故事和倫理思考,讓讀者得到相關知識,從而更能關心在性傾向上面對掙扎的朋友;同時又可從倫理角度討論同性戀議題中出現的爭議,陳述近半個世紀的同性戀社會運動對社會、文化、教育、宗教等造成的深遠影響。
小冊子嘗試從三個與「同性戀」相關但容易混淆的層面討論,亦希望相關概念得以釐清:
同性戀即指個人在性傾向上感到自己對同性(男/男、女/女)在情感上、愛情上或性上出現持續性的吸引。對於同性戀的成因是先天還是後天,眾說紛紜。有人傾向相信自出娘胎便已決定,有人則認為成長經歷或所身處的環境有所影響。且看看不同的學說如何理解同性戀的出現。
如前文所述,性別認知及性別傾向兩個階段所認知的規範會影響個人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發展,所以當我們談論同性戀的後天因素時,便需探索有什麼影響着性別認知及性別傾向的發展。學者指出成長過程中經歷性別不確認(gender nonconformity),成年後較多人自稱為同性戀者。[18]
成長經歷──家庭(父母角色、父母關係、與父母的關係)
4.2.1 父母角色
父母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影響兒童對性別的認知。有學者指出一般同性戀者的父母都傾向有某些特質,母親會向子女表達過多的愛,而父親多數不參與在家庭中,母親比較主導,父親比較軟弱。[19]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會模仿父母,所以父母親的性別角色很影響子女對性別的認知。父親對孩子的肯定和保護令他們建立起自我認同,能在成長過程中對男性建立信心、同時找到男性角色的模仿對象。母親對孩子適當的回應和關愛亦能讓他們建立對女性角色的認知,從母親身上學習如何成為女性。
男性與父親關係疏離,他們認為自己被父親拒絕,但心中渴望父親的愛,故會轉向從其他男性身上獲得認同及被愛,以補償缺乏的父愛。重男輕女的社會觀念令女孩子容易被忽略,潛意識中對女孩子的身份不能接受。在充滿單一性別成員的家庭環境成長(如:父親早逝,或其他家庭成員大部份都是女性),都會對孩子的性傾向有所影響。
4.2.2 父母關係
父母之間的關係,對兒童建構性別認同有著重要的影響。
Evans曾進行相關的研究,他指出男同性戀者的母親一般與父親的關係很疏離,對父親很冷漠,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兒子身上,希望聯同兒子一起對抗父親,甚至阻止兒子在青少年階段與異性建立關係。[20]
母親經常對父親不滿,常常批判、藐視、甚至羞辱他,更不停提醒兒子不要學效父親,令他不能認同父親的男性角色,可能會令他對自己的男性氣質感到羞愧,甚至對女性感到抗拒。同樣,父親常羞辱母親會令女兒覺得母親(女性)非常懦弱,覺得做女性很不安全。令她潛意識地抗拒女性,拒絕認同自己女性的身份。
4.2.3 與父母的關係
根據不同學派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ies),嬰兒期已需要與人建立關係,所以父母或照顧者對嬰兒成長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嬰兒透過與父母或照顧者的接觸,學習如何理解人的情緒、想法、期望等。這個階段的嬰幼兒極度害怕與父母或照顧者分離,Ainsworth指出父母對嬰兒的不同回應,會引致嬰兒發展出不同情況的依附,影響他們與人建立關係的情況及其行為表現。[21] Bartholomew & Horowitz根據Ainsworth的理論,研究長大後的人際關係如何受影響。[22]
無論有多少學術研究作為引證,同性戀運動團體都仍然堅稱同性性傾向是不可改變,背後原因是:若可以「轉變性傾向」(下稱「轉變」),就會抵觸了他們的基本前設:同性戀是天生的,健康及自然的傾向。
這些逾越同性戀運動底線的事實,受到部份激進的同性戀運動團體激烈地攻擊,並將任何協助同性戀者自願尋求「轉變」的臨床治療和輔導污名為「拗直治療」。[26] 而所謂「拗直治療」,其實就是上世紀的「厭惡治療」(aversion therapy)──把希望戒除的特定的行為與不愉快或懲罰性的刺激結合起來,達到戒除或減少目標行為的目的。
然而,對今天的同性戀輔導來說,「拗直治療」是張冠李戴。今天的臨床治療和輔導的方向主要是按照同性戀者個人的意願,陪伴同性戀者一同處理他們生命中的傷痛,重新尋找個人的身份及認同,建立整全的健康人生觀,或許他們會因此而「轉變」,但輔導的過程中不會亦沒有可能強迫他們作出非自願的改變。
不少臨床研究顯示,同性戀者可以透過不同的輔導減少同性的性吸引,甚至有人透過重建個人的性觀後,嘗試過健康的異性戀生活。
但始終有關「轉變」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以下是近幾十年部份對於「轉變」的相關討論:
Haldeman於1994年撰文批評過去一些有關性傾向轉變的調查報告的調查方法並不嚴謹、表示有聲稱已「轉變」的人仍有同性性吸引,所以過去的報告都是「充滿異性戀的偏見」、「有恐同症」的,結論並不可靠。[27] 1999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美國心理學會等組織印製有關「轉變」性傾向的小冊子,指責「轉變」不但成效不顯注,更會引起同性戀者的罪惡感及焦慮。
然而在學會中有數位精神醫學博士聯署去信反對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結論,表示小冊子誤導其他人對「轉變」治療的了解、忽視有同性性傾向人士需要在適當的幫助、諮商下確立性傾向的需要、甚至妨礙精神科醫生的執業自由,在壓力下不敢為同性戀人士進行相關治療。[28] 信中亦提及在1994年Macintosh進行了一項比較嚴謹及大型的調查,285位精神分析師指出,曾經接受他們治療的1215位同性戀者中,23%由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者,另有84%的人士獲得明顯的改變。[29]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美國心理學會與其他心理學會的一些前任主席亦批評,美國心理學會太受政治正確影響。其中1985年美國心理學會主席Perloff 就批評:現在有關的資料尚未全面、若當事人真的想改變,應先尊重及聆聽當事人的意願,一面倒的政治主張會阻礙有關的研究。
隨後,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及行政院長亦澄清他們的立場:個人的意願應得到尊重,若個人滿意於自己同性戀的情況,治療員的角色不是去遊說他們改變;但對於那些想改變性傾向的同性戀者,治療員應提供協助。[30]
1998年,Throckmorton綜合過去的研究報告,得出結論:協助希望「轉變」的同性戀者改變自己性亢奮模式是有效的,更應為尋求幫助的人提供相關的治療。[31]
美國國家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 NARTH)以兩年時間研究了860個決心「轉變」的人士,發現他們大部份能成功改變了性傾向。[32]
Nicolosi等人研究了689男及193女曾接受治療的同性戀者:治療前67%表示自己是(完全或接近完全)同性戀,治療後只餘下12.8%,34.3%轉變為(完全或接近完全)異性戀;除了性傾向轉變外,更表示經歷了心理和人際狀況的改善。35.1%未有「轉變」,但同意情緒比前更健康。[33] 其後,Byrd等人就上述的研究作跟進,發覺同性戀者主要希望在幾方面得到醫治:感情需要的缺乏、家庭和社交關係的缺乏和被侵犯後的影響。[34]
200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前主席Spitzer出版他對同性戀者改變性傾向的可能性的研究報告。研究使用sexual attraction scale 和sexual orientation self-identity scale作量度基礎,結果顯示,200名(143男,57女)曾接受輔導/治療的同性戀者,當中66%(男)及44%(女)表示能發展「良好的異性戀功能」(good heterosexual functioning),沮喪及抑鬱的程度顯著降低了。[35] 治療前,沒有人說表示自己的性傾向是絕對異性戀,46%男和42%女表示自己有絕對同性戀傾向。治療後,17%男和54%女表示自己有絕對異性戀傾向。
接受治療者希望「轉變」的原因:認為同性戀生活未能令他們得到情感上的滿足(81%);與自己的價值觀或宗教信仰有衝突(79%);希望可以結婚或維持現有的異性婚姻(67%男,35%女)。
Spitzer的報告引起廣泛討論:
2001年進行研究前,Spitzer支持性傾向是不能改變的。
2004年,他在一段短片中表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可視為精神病學的『聖經』。1973年,我提出了同性戀不是精神病的定義。同性戀運動的活躍份子(按:就言論)採取了策略性的政治立場,為了可以更好地說服社會大眾──當有人是同性戀,他是絕不能改變的。我理解和接受這政治觀點可以幫助他們宣示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我認為這(按:同性戀不能改變)就是不真確(not true)。」(由編者翻譯)[36]
2003-2007年間:不斷有人挑戰報告的論說。
2007年:Spitzer重申如他人要引用當年的研究結果,指出性傾向可以改變的同時,必須指出「成功個案是非常罕有的」。並提醒考慮參加有關項目的同性戀者,要清楚知道改變的機會非常低。[37]
2012年: The American Prospect的一名記者撰文“My so-called Ex-gay Life”表示自己因相信Spitzer的研究報告結果,於是接受相關輔導但失敗,[38] 該記者更聲稱事後訪問Spitzer有關他的研究。報道描述Spitzer承認該研究的結論只限於描述「有證據指經驗過輔導的參加者認為自己有改變」,而非證明治療的效用。
同年,Spitzer去信《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主編Zucker,表示認同當年的研究存著致命的爭議:無法判斷受訪者對性傾向改變的自述的真偽。他表示能合理地解釋如何假設同性戀者的自述並沒有說謊,但事實上無人能夠百份百肯定受訪者沒有說謊。並表示令同性戀者誤會當年的報告已證實治療成效而深感抱歉。
同年,在一段由同運網站TruthWinsOut.org剪接而成的片段中,Spitzer重申他在報章中對受誤導的同性戀群體道歉,並希望PFOX及其他機構停止引用上文提到在2004年所錄製的短片,作為「Spitzer贊成同性戀能改變」的論據。(片段載於YouTube “Dr. Robert Spitzer Retracts 'Ex-Gay' Study and Apologizes to the LGBT…”,http://www.youtube.com/watch?v=gIifMxPcRnI )
1940年,Kinsey(金賽)提出同性戀者佔人口的百分之十,然而他的研究樣本很多是囚犯,當中大部份是性罪犯,所以數字明顯過高。根據最新的研究顯示,不同的地方大概有百分之二至四(2%-4%)的人是同性戀者。[49] 不管同性戀者的人數有多少,我們是否認同同性戀,我們都應該尊重他們的基本權利。大家應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討論同性戀議題,切勿惡意攻擊持不同聲音的人士。
同性性傾向與同性性行為之間並沒有等號。
首先要清楚分辨同性性傾向(即經驗到同性間吸引),以及同性性行為(有同性戀愛或同性性行為)兩者。同性戀者會因應同性性傾向,而傾向尋求與同性建立同性情愛關係及發生同性性行為。然而,有同性性傾向的人,並不一定會有同性性行為。正如有學者認為所有男人都有性濫交的傾向,但很多男人並不會選擇去濫交。另一方面,曾有同性戀行為的人亦不一定有同性性傾向,有些可能因著貪新鮮、刺激,有些可能受到同性戀朋友或長輩驅使。
成長過程中的男女很容易出現性傾向疑惑,特別當他們發現自己有很尊敬或仰慕的同性長輩、或同性好友因其他人而忽略自己而妒忌,很容易會誤會自己愛上對方。同性性傾向是指人在「性和愛」方面明顯地持續對相同性別或某一形式的吸引感到渴求,即會渴望與對方有進一步的親密的性接觸。若你只是想進一步認識對方,而沒有持續地有性和愛的吸引,那應該不是同性性傾向。有些情況是,一些人的同性性傾向或行為只是暫時的。如身處在充滿同性而缺乏異性的環境,而在當中又渴望得到情感上的依附時,也可能會導致出現假同性戀:監獄、軍隊、男校或女校便是一些較普遍的場景。當對性傾向的發展出現疑問時,建議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切勿道聽途說、胡亂猜測或嘗試。
雖然同性性傾向並不一定是自己可以選擇,但並不代表因此要過同性戀生活或有同性性行為;即是說無論任何人都須要為自己的選擇及行為負責。讓我們看看同性戀行為會有甚麼影響。
外國有不少研究和統計,都顯示過著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人士,要面對不少健康問題。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在1973年因美國心理學會的要求,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剔除,原因是他們表示同性戀是天生,無法改變,但其實不斷有學者反駁當中的論說。我們無法辯論當時的提議到底是否正確,但當時的背景及風氣或許對整個情況有著一些影響:
1973年前:美國心理學會建議用投票方法去決定同性戀是否病態,然而卻未有提供實質的研究數據支持論述,投票期間,支持同性戀運動的團體(下稱同運團體)不斷作出滋擾,研討的過程未能順利進行,是次會議似乎亦以非慣性的速度進行。
1973年美國心理學會的二萬五千名會員之中,只有約三分一人回覆(58%同意剔除,其餘42%反對)美國一些不接受這立場的醫生根本沒有理會是次決議。
1977年,醫學期刊向10,000位美國心理學會員作隨機訪問調查,當中69%被訪者認為「同性戀」是「病態的適應」(pathological adaptation),另有13%表示不能確定。
有輔導員、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和學者等並不同意美國心理學會的建議,組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NARTH),繼續就同性戀進行研究工作,而他們最近亦進行一個很詳盡的研究和分析,結論是:同性性傾向不是先天的,是能改變的,治療同性戀不見得有害;而同性戀生活方式與精神和身體的病態的確有更大的關連。[71]
另一方面,1957年Hooker發表的The Adjustment of the Male Overt Homosexual調查報告,[72] 經常被引用支持同性戀並非心理病態等主張。今天回顧這份報告時,發現當中的漏洞:
調查的對象:向同志團體徵募「適應良好」的同性戀者做測試,必須是沒有進行精神病或心理病方面的輔導或治療,樣本出現偏差(sampling bias)。
Hooker使用rorschach test、TAT和MAPS測驗,令研究對象預先知道研究想達到的目的,以致預期的結果出現。
近代研究反駁:同性戀者普遍於個人困擾、憂鬱、自殺意念、酒精及藥物濫用方面,以及感染疾病方面的數字明顯偏高。
我們不以同性性傾向是否病態作為爭論,因為同性性傾向的成因實在複雜,不可以一概而論。但重點是我們要察驗我們對有同性性傾向的人的態度,如何尊重、不批判,卻又可以給予幫助、同行。
2007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男同性戀者McKellar如常參加男同性戀者舉辦的活動,卻令他漸漸關注將肯定同性戀行為的意識形態強加在社會上是錯的。加拿大的奇幻樂園(一個類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主題公園)推出一年一度的同性戀日(讓同性戀者這天在樂園內結集,自由地手拖手在主題公園鼓勵的旗幟下親密示愛。),它的第一年順利舉行。
翌年, McKellar成立了一個「同性戀者反對極端驕傲主義」的組織並在樂園的同性戀日舉行時進行反對示威,同性戀日從此沒有舉行。他認為主流社會沒有必要認同同性戀行為和被迫接受同性戀與異性戀具同等社會效益的論述,也不認同在社會中積極推動肯定同性戀行為的意識形態。 [79]
前女同性戀者Cothran的經驗。她寫道:「在我過去29年的生命中,我一直是一位對男女同性戀議題進取地,富有創造性和戰略性的支持者。我已經舉辦和參加了無數的遊行和各種遊說工作,爭取平等對待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我一直跟進有關的議題和對一些進行我認為使我最激動的工作的組織作財政捐助。作為一本有十三年歷史,目標是黑人同性戀者的期刊的出版商,我有機會公開向數以千計的人發言,影響藏在衣帽間的人走出來,為自己站起來,這對非洲裔美國人社群中是特別困難的。
但現在,我必須再一次走出衣帽間。最近經歷改變的力量充滿我,當我完全降服在耶穌基督的教義下。作為一個信奉上帝話語的人,我完全接受,並一直知道,同性關係不是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心意。」[80]
Cothran出版《Venus Magazine》為黑人男女同性戀者發聲。雜誌曾兩次獲優秀文學獎,銷售量已上升到每期38,000份。有同性戀的經驗並不意味著當事人要支持同性戀運動。
看看前男女同性戀者的見證,閱讀一下甚至有20多年的同性戀經驗的人如何能夠離開這種生活模式,您會知道得更多。
同性性行為是指有同性性傾向的人士之間涉及性的親暱行為,不限人數,不一定有愛的關係,可以是純粹性愛的歡愉,交合方式不限。過去同性性行為一直都被視為不道德,然而近年有主張自由主義的學者表示同性戀行為不存在道德的爭議,同性性行為,該在道德層面上的什麼位置?
西方很多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康德等,還有宗教立場(基督教、天主教)都認為同性戀行為是罪、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同性戀行為是一種逆性的行為,即違反自然、違反人本性的行為。
中國的儒家思想重視陰陽調和的婚姻觀念,故不贊成同性戀。而佛教就認為,一切夫婦關係之外的邪淫都是罪;即視一切男女夫妻之外的性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釋聖嚴《戒律學綱要》)
然而,近來有學者對這些哲學家、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觀點提出反駁。他們反駁究竟甚麼是「自然」呢?為甚麼同性性行為是不自然呢?有人用右手寫字,有人用左手寫字,左手寫字又是不是違反自然呢?
按現時自由主義的理論,一切行為只要是「雙方同意」而又沒有「傷害他人」,基本上就沒有道德問題。所以他們認為雙方同意下的同性性行為是沒有道德問題的,甚至是一種偉大愛情的表現。
但自由主義的觀點同樣受到批判。反駁的論點是質疑是否一切行為,只要「雙方同意」和「不傷害他人」,就沒有道德問題呢?按此推理,只要雙方同意,成年人的亂倫、濫交、甚至人獸交等行為豈不是也沒有道德問題?
基本上雙方的爭論點在於:
從生理結構來看,沒有人會否認男女性器官的配合是最理想和最自然的。從人類學層面看,男女結合才能繁衍後代,是自然的歷史進程。無論你對同性戀的態度如何,我們強調同性戀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縱使我們未必同意他們的行為,仍要尊重他們作為一個人,應享有一般人基本的權利(如:言論自由、接受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亦反對對同性戀者不合理的對待。但由於很多研究顯示同性戀的行為及生活方式在健康及倫理道德方面有不少問題,所以我們不認為同性性傾向人士必須以同性戀生活方式生活。
如前文所說,同性性傾向的成因、性傾向能否改變,都有不同的論說,未能百分百確定。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當同性戀者願意向你講及自己的性別角色混亂或性傾向時,無論你認同與否,你都可以做到的是:聆聽與尊重。倘若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覺得仍未調整心態去分享他們的「秘密」,以平和、友善的態度表明便可。
至於面對同性戀者的同性情愛關係及其行為的影響,我們未必能夠阻止。然而,作為身邊人需對他們作出提醒,勸誡同性戀基督徒思考自己當如何在信仰中自處,如何面對當中的衝擊,又如何克服當中的情慾試探,以跳出同性情愛關係的枷鎖。有些時候,你會很熱心希望幫助朋友不再活在同性性行為的陰影下,然而你的朋友不一定會接受你的幫助。時間、認知、感覺上的發展都會影響他們的意願,勉強未必達到果效,反而持續的關心及包容更加重要。
當你的學生或案主決定向你提及自己對性別角色定位的疑惑、或同性性傾向時,他/她或許正在混亂與掙扎中,他/她或許已鼓起很大的勇氣,他/她或許正承受很大的情緒困擾。作為專業的青少年工作者,你可考慮以下方法幫助他們:
我們所指的同性戀過來人,實際是一些已悔改,脫離了同性戀生活方式的基督徒。他們定意離開同性戀的誘惑,將生命交託給神。因著信靠神,他們低落的自我形象及同性戀的轄制,逐漸得著改變。
男同性戀過來人一般比較被動、自我、孤獨、需要但又害怕和人(尤其男性)建立親切的朋友關係。部份則和異性相交有如姊妹般,親密、倚賴,卻並非戀愛關係。他們懼怕和男性建立友誼,他們覺得自己比不上對方,既羨慕又恐懼。然而,同性戀過來人就是要面對自身的恐懼,在神裏重新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7.1.1 給弟兄們
因過往的傷害,同性戀過來人對自身作為男性仍然抱著懷疑,他過去的表徵就是用扭曲的方法(如情感倚賴或同性戀行為)來滿足對同性認同的渴求。
他性格被動,在教會中很容易成為弟兄姊妹主動「扶持」婚姻的對象。筆者就曾經在弟兄一次又一次親切的「查詢、鼓勵和關心」下,冒險地剖白了自己的苦衷。結果在對方態度霎時的轉變下,再次受傷。
弟兄們,當有弟兄告訴你他同性戀的秘密時,他在矛盾中已掙扎了很久,他可能在向你「求救」。請不要離棄他,也不用感到壓力。你只需要以平常心和他保持一貫的相交模式,這對他已是莫大的接納和治療。請不要套用一般勝過試探的方法來「教導」他,也不要不時用「現在可以開始拍拖了吧?」等等來判斷他究竟成長了沒有。要知道,成長的果實不一定是婚姻,乃是終生學習靠主;不單是不再受同性戀誘惑的捆縛,乃是全人的靠主成聖。
請多參考一些基督教有關同性戀產生及改變的書籍,了解他所面對的,並引薦他進入一些弟兄姊妹們的團體活動中建立人際關係,作他的榜樣,這對患得患失的他將會是極大的鼓舞。
如果你發現他開始對你有情感倚賴甚至慾望,你要堅決地表示你不接納這些違背神的行為,但你亦要表示你接納他是神裏的弟兄,是你的朋友。在他同意下,可與教會成熟的基督徒分享,與他同行祈禱,或有需要時轉介到合適的輔導,最重要是保持不變的朋友關係。
7.1.2 給姊妹們
外表成熟又未有女朋友的弟兄,很容易成為未婚姊妹們的婚姻對象。但他實在還有很多成長包袱:他尚在學習更親近主、不再受同性戀轄制、放下自卑,並且正由過往倚賴女性,轉化為平等朋友關係的過程中。然而,很多偏差的期望卻由此而生:他視她為好朋友,她卻視他為發展中的男友。同性戀過來人可能尚未體會那些言行舉止會帶來誤會,他一方面盡吐心聲,一方面卻說姊妹只是他好朋友。但女方既已認定目標,便以為自己女性的愛可以「溶化」弟兄。
姊妹需要了解弟兄目前欠缺的是健康的男性關係,這是女性無法取代的。她若心急逼迫,換來的可能是毀了的關係或勉強的婚姻。
姊妹們,當有弟兄告訴妳他同性戀的問題時,他可能只視妳為知己,請不要以為這是拍拖的前奏,請先多了解有關同性戀的問題。妳亦找牧者諮詢,但妳不能取代其他男性對他成長的重要性。妳要了解他面對同性戀試探的態度,亦要格外留意他的倚賴和令人誤會的身體語言。在這過渡期,作為朋友,妳的支持可能會帶來一個很健康的主內弟兄姊妹關係。
7.1.3 給基督徒夫婦們
同性戀過來人的成長,普遍地經歷不健全的兩性關係,特別是過往父母的溝通模式,深深地影響著他對兩性親密關係的信任。如果有成熟的基督徒夫婦願意守望同性戀過來人,作他的支持及榜樣,這將會是莫大的幫助。
7.1.4 給牧者們
很多同性戀過來人孤寂地尋索一個可棲身的教會。牧者是教會的領袖,他儼如一個父親,是一些同性戀過來人既懼怕又想親近的同性對象。
牧者們,在適當的場合,請帶出主內平等和接納的訊息。在你有限的時間,你未必會與他們建立友誼,但你的不定罪、遮蓋、甚至是間中的關懷,可能是同性戀過來人與父親和好的一個投射,他得到的醫治,你會始料不及。
7.1.5 給反對同性戀的基督徒們
在現今同性戀風氣日趨泛濫的年代,為神,為教會,為時下青年,我們一班基督徒必須站起來,勇敢地抗衡這些倡議同性戀的歪曲言論。然而,有些基督徒的激進言論,側重同性戀行為的罪行和污穢,沒有帶來憐憫和改變的出路,只有理論層面的聲討筆伐,卻造成兩極化的對立局面。這樣,爭取公義是一回事,卻徒然加添當中尋求改變者的自卑和旁人對他的戒心。
要知道沒有一個人孩提時候就決意選擇同性戀的。逐漸成長的他,當面對無法解釋的同性戀感覺浮現時,他本來已有點徬徨。在沒有出路的對立下,有些更因此戰兢地走上表面上接納他的同性戀不歸路。
反對同性戀的基督徒們,請記著,我們都是罪人。要知道你的受眾中,有人可能正在暗自垂淚,他們需要的不是繼續定罪,而是在神裏的出路。你豐富的知識,你可建造的橋樑,還有轉介,將成為他們踏出第一步的極大幫助。
7.1.6 結語
然而,這裏欲帶出的訊息,是同性戀過來人的改變和成長,是一條漫長的路。他需要在神裏的盼望、他需要聖經真理、他需要積極投入、他更需要你的接納。你願意去了解和明白更多嗎?願我們互勉,在成聖的路上同行。守望同性戀過來人,作他的支持及榜樣,這將會是莫大的幫助。
同運的英文名為LGBT movement,見字得義,同運一直爭取的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和變性人/逆性人士/跨性別人士(transsexuals),近年亦常有將酷兒(queer)、陰陽/雌雄同體(intersex)、尋覓性傾向中(questioning)、無性別(asexual)等,都放進同運的議程中。同運努力擠身弱勢的一群中,以「小眾」作為包裝,並在社會中尋求法律上特別的保障。然而,同運並不接納後同性戀者(post-gays、post-lesbians)。
我們要區分個人決定與政治制度。自由戀愛的氛圍下,戀愛是個人決定,沒有人可以強行迫使對方進入戀愛關係。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我們都不反對同性戀者自由戀愛,亦不能阻止。然而,婚姻作為社會制度,就超出了個人自由的討論層面。
不是所有形式的婚姻制度都受人權法所保障,[85] 過去婚姻法反映社會視一夫一妻可為下一代提供健康的成長環境,為社會的重要基礎,視之為社會共善(common good),所以特別以法律和福利去鼓勵這種結合。
如社會要訂立某種婚姻制度,就等於要社會都認同和肯定,某種形式的結合是最有利社會和家庭的。然而,我們並不認為同性「夫婦」關係,對社會和兒童的發展比一夫一妻更達至社會共善。
補充一點: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人身安全、自由和基本福利)應受保障,現時亦已受法例保障:同性戀的非刑事化已通過多年了; 申請公屋、公職等並不考慮性傾向(也不用申報)。
極端自由主義者忽略社會的共善(common good),而這正是衡量婚姻制度的處境。他們忽略生活方式的美善與否,認為所有生活方式都應平等看待,這種進路導致社會問題叢生。一些溫和自由主義者如Macedo也有所反省,並提倡judgmental liberalism──敢於作價值判斷的自由主義。相反,單用公平角度看婚姻制度,可以產生很大的問題。例如:成年人可結婚但兒童卻不可,這便是不公平。
不應以輕蔑的態度對待傳統:婚姻制度如此重要,在悠久的歷史中不斷經歷修正和試驗,才有今天人權所保障的異性、二人婚姻制度。或許可參考保守主義的觀點,作出中肯的評價:難道我們這個時代所謂的人權公平概念必定正確?幾千年累積的人類經驗和智慧卻一點參考價值也沒有?
本文摘錄於由Jeffrey Satinover醫生所寫的「基因和環境的複習交互作用:一個同性戀的典型。」一文。原文章已在1995年由美國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國家協會收集。
我們或許不能完全掌握基因、環境與其他因素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可能會有一特定因素影響事情的結果,但它不是引發事情發生的原因,我們亦難以確定它扮演甚麼角色。以下的情節是由許多真人故事改編並輯錄而成,旨在說明各種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人的行為。
(注意:以下只是云云可以引致同性戀的其中一項原因;然而,它們卻是十分常見。事實上,不同原因可促使人有某種性表達,縱使它們看起來十分相類似,但其實卻是非常個人化的。)
先天因素是其中一個促成原因。一個具有同性性傾向的男孩可能擁有一些常見的同性戀特質,而這在一般人身上並不常見。這可能是出於遺傳,也可能由「子宮內的環境」所引起,如賀爾蒙。沒有擁有這些特質的兒童,長大後會稍為不易成為同性戀者。這些特質包括:敏感、澎湃的創造力及敏銳的美術感等。當這些特質十分強烈時,或許會成為一些心理特徵,甚至為人帶來煩惱。
然而,沒有人能確定哪些才是與生俱來的特質。不過我們對此仍有一些亮光:如果我們能在不受政治議程及爭議的影響下認識同性戀,相信可以釐清這些問題—就正如現在在這裡般。無論如何,現在並未有完全的數據去證明同性戀是天生的。
在幼年時期,這名男孩或許已擁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質,令他在大伙兒中顯得格格不入。他可能是較為害羞,但他的同儕卻是典型的「粗魯」男孩,因此與他們相處時男孩會感到不自在。又或者,他對閱讀及藝術感興趣—但這只是因為他是個聰明的孩子。男孩成長以後,當他回顧這些兒時的經歷時,他將會發現自己很難分辨哪些是出於其天賦的氣質,而哪些則是其他原因。
不知甚麼原因,當男孩日後回憶起與父親的關係時,他會發現一個令自己痛苦非常的落差:父親對他的愛遠不及他所渴望般。可能大多數人會同意這名男孩確實與他的父親十分疏離;但亦可能有人認為男孩的父親是一個相當好的男人,只是這小孩的渴望太特別了,當父親的根本難以找出一個合適的方法與他相處。又甚至乎,這位父親真的太討厭兒子有著如此敏感的特質。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男孩確實與父親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缺乏快樂、溫暖與真摯,而且也使男孩十分失望。同時,這狀況驅使男孩對父親採取防衛的態度,並且決定要疏遠他,目的旨要保護自己。
可惜的是,若這男孩離開他的父親,並否認自己對男性模範人物的需要,結果只會令他更難與其他男性同儕相處。可能有人會將他與一個喪父的男孩相提並論,比較誰較不易成為同性戀者並因此受傷害。然而,在前男同性戀者身上發現,他們成為同性戀者並非只因喪父。原因而是在於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父親失望,並重複不斷地對父親採取防衛的態度。事實上,一個沒有對父親採取防衛態度的男孩(也許是因為他天賦的氣質,又也許因為早期受到充足的治療;甚或在他生命中出現了另一個重要的男性模範人物) 成為同性戀者的機會會較低。
男孩與母親之間的動力亦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它可以填補父親在男孩心中的不足。因為人傾向與自己氣質相近的人結伴,所以男孩有可能發現自己與父母親並不親近。
因著這些理由,一個成年的同性戀者回憶起他的童年時,他會如此道:「從孩提時我就是與別不同。我從來不能與同年齡的男孩愉快相處,只有與女孩子相處才感到舒暢。」。這段記憶會使他日後更確定自己是早已被安排成為同性戀者的。
雖然男孩對父親採取防禦態度並疏遠他,但他仍會默默地渴望父親的擁抱,實現他心目中那理想的父親形象。在孩童時期,他對於那些欣賞的年長男孩會產生一種強烈而不帶有性慾的依附情感,這感情是隔著距離的。這重複了他對父親的渴望及那種遙不可及的經驗。其後男孩會步入青春期,性需要亦開始萌芽,他希望可以把自己依附在任何人身上—特別是在男性上。男孩的性需要與他對男性的強烈渴求結合,他希望可以與其他男性發展一段親密和溫暖的關係。因此,他開始發展了對同性的迷戀。日後,男孩會如此回想他的青春期:「我第一次對性的渴望是在男孩而非在女孩身上。我從來就對女孩子沒有興趣。」
於這時甚或更早的時候進行心理治療可有助男孩避免發展成同性戀者。男孩的柔弱性格源於他拒絕接受及認同那被他拒絕的父親。心理治療可助男孩改變這仍在發展中的柔弱性格。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讓父親知道,他該如何與他的兒子建立一段合適的關係並參與他的生活。
在我們的文化中,青少年性行為及婚姻以外的性關係是被認可,甚至是鼓勵的。這位男孩已漸漸成熟,他現在是一個十來歲的青少年了,他開始嘗試參與同性戀活動。或許,他的同性戀需要已被一個較年長的男孩或男人所利用,在他仍是兒童時已視他為獵物。(請參考相關的同性戀研究,當中發現兒時受性虐待的經歷會深深地影響兒童日後成長。) 又或許相反地,儘管男孩被其他男性所吸引,但可能出於恐懼和羞愧,他會極力避免牽涉此等活動。無論如何,儘管他正為自己的性渴望強烈掙扎,但他總不能否認那些渴望。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掙扎只是一個「選擇」,將會是非常殘酷的事。
男孩的確記得那段苦惱的日子:他否認渴望的存在,甚至希望拋棄它們。可是全都沒有用。我們可以輕易地想像,若果日後有人不經意或魯莽地指責是男孩自己選擇當同性戀者時,他將會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去生氣。當他尋求幫忙時,他會聽到以下兩個訊息,而兩個都在恐嚇他,一是:「同性戀者是壞人,而你是一個壞人因為你是同性戀者。這裡沒有你的容身之處,神並且要懲罰你,要你受苦,因為你實在太壞了。」另一個則是:「同性戀是天生而且不能改變,你生來就是這樣子。你希望結婚生子?好比要住在一棟有白色圍牆的小房子,這只是在神仙故事中才會發生的事。你最好忘了它。是神使你有今天的結果,你是命中注定的。學習享受它吧。」
終於在某一個時刻,他屈服於自己那份對愛的渴望,因而開始發生同性戀行為。雖然這使他恐懼,但是昔日那些深刻及痛苦的渴望只是暫時性,現在他第一次可以感到輕鬆一點。他或許感到極度掙扎,但是不得不承認這又是極大的解脫。這一次暫時的安慰使他十分深刻,遠超過簡單的性興奮所能提供的。這經驗正在強化他的同性戀行為。後來他會發現無論如何努力控制自己,最後都會被一種力量驅使他重複上述經驗。當他再次重複,那行為便會再一次被強化,而他亦有可能再次做同樣的事。最後,他對同性戀行為的掙扎轉趨冷淡。
與其他人一樣,他發現性高潮可以有效地舒緩一切的壓力。投入同性戀活動意味他已打破一個眾所周知的性禁忌。現在他可以輕鬆地打破其他禁忌了,濫交便是其中一種。假以時日,當他逐漸投向同性戀活動時,它很快成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環,甚至支配他的生活。事到如今已不再和初期一樣僅是出於他對父愛的渴望,現在那是用來減輕所有的焦慮。
隨著時間流逝,這人大部分的生活時間會變得更痛苦。就正如在很多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身上所聽到的一樣,別人冷酷無情的對待是令同性戀者感到痛苦的原因,他們甚至會被公開地敵視,唯一能夠接受他們的就似乎只有其他同性戀者。因此,這群同性戀者便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社群。然而,同性戀者經歷到的壓力並非只如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所言般。壓力很多時是由他的生活方式所引起。如:在醫學上,同性戀者有患上愛滋病的可能—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後果。他將不能避免地因自己的濫交行為而感到罪疚和羞愧。同時,他亦知道自己不太可能與異性交往及建立家庭。雖然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極力利用政治手段去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但是領養權和遺產權都不足以彌補這些人心理上的失落。
雖然很多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嘗試將典型的同性戀行為及其所帶來的傷害正常化,並會因政治目的而使用權宜手段,向公眾隱瞞這些傷害。但是,除非他埋沒自己大部分的情緒感受;不然,他實在不能在這情況中真誠地因著自己而感到滿足。對他而言,最嚴苛的譴責並不是出於恐同者死硬派,而是出自他自己。而且,他每天也因著自己擁抱同性戀而掙扎,不斷譴責自己,甚至達至自我貶抑的地步。雖然他身旁的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會說他只是受周遭的「恐同」氛圍影響,但是他深知事實卻不然。
「同性戀者」這個身份會成為他的壓力,而且會導致更多的同性戀行為。也許會有人對此覺得驚訝—至少是那些沒有典型行為的人。最典型的行為是強迫性自慰。他們會沈溺其中,不能自拔。自慰行為會為他們帶來罪疚、羞愧感及自我否定,結果只會增加這行為。若他以為可以否認這些情緒,並且可免受它們的影響,這並不奇怪,他的確會這樣做。他會這樣告訴自己:「那(自慰) 不是一個問題,因此不需要為此感到難受。」
經過多年與罪疚及羞愧感搏鬥後,男孩現已長大成人了。長時間對自己的否定使男孩現在相信:「無論如何,我不能改變我的同性性傾向,因這是不能改變的」。若「可以改變」這個念頭在他腦海中閃過,他只會痛苦萬分地想:「如果可以改變的話,為甚麼我卻不能?」只要腦海中稍稍出現這意念,那些羞愧感又會回來了。因此,當男孩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士之前,他已經整理出這個觀點:「我總是與別不同的,也總是個局外人。自我有記憶以來,我便已經迷戀男孩。我的初戀對象是一個男孩而不是女孩,我對異性沒有興趣的。哦,我也曾努力嘗試與女孩子發生性行為,但那只是平淡乏味,遠比不上與男孩發生性關係。與男孩第一次發生同性戀關係卻使我知道那就是我所需要的。因為以上的經驗,我強烈體會到同性戀是遺傳的。我曾經試過改變,上帝也知道,可是總是徒勞無功。原因在於那根本並不可以改變。最後,我不再嘗試改變反而接受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同性戀是天生而且不能改變」這觀念或多或少是因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而造成。對這男士而言,這觀念更決定了他在青春期的成長。蔓延全球的同性戀正常化觀念加上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思想,在男士的青少年時期更鞏固他的信念。不過這並不可一概而論,有些早前我們曾談過的例子中,以上的因素不甚明顯。別人的嘲笑、責難及嚴厲的懲罰亦有可能使他陷於這樣的景況中。
如果這名男士仍然渴望傳統的家庭生活,他很有可能會陷於昔日的掙扎中。然而,他遇到的環境會影響他作出怎樣的改變。一般的機構或宗教團體可能會責難他,令他難堪;另一方面,同性戀運動活躍份子則會嘗試左右他。在這時,「治癒是有可能的」會是對他最重要的說話。
若這名男士選擇治療,希望投入異性戀的話,這意味著他將會踏上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完成這段道路所需的時間,可能會比起一段婚姻所能維持的日子更長—特別在現今美國社會破碎的婚姻關係比比皆是。
進入治療後,他會開始理解自己那些渴望的本質並非出於性,而他這個人也並非只由性傾向所決定。在這些大前提下,他可以學習如何與其他男性相處,建立一段不涉及性的純友誼親密關係。此外,他亦可以學會如何與女性相處相交,無論是建立友誼、戀愛關係,甚或締結成為生活上的伴侶。
可是,舊傷疤並不會全然褪去。日後當這男士遭受壓力時,昔日的想法及行徑又會浮現出來。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他的同性戀及性傾向永遠都不能改變。隨著新生活的展開,他開始與他所愛的女性建立一段親密的關係,都有助他的生命更趨向整全,而那些昔日在他腦海迴盪的舊想法亦會減弱。
經過一段時間後,他會發現那些渴望確實與性沒有關係。因此,他會重新正視它們,同時亦開始尊重自己的感受。可是,它們亦會成為暴風雨前夕的警告,提醒男士其原生家庭的混亂,又或是在他心裡存在已久的渴望及拒絕,並會再次恢復防衛態度。然而,當他的家變得井然有序時,那些舊有的控訴會隨之消失。朋友、丈夫及專業人士等身份成為他甚至是其他人的祝福,它們不再是詛咒了。
[2] 吳敏倫:《香港性經》,(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63。
[3] J. R. Udry, N. M. Morris and J. Kovenock, “Androgen effects on women's gendered behavior,”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7, no.3 (1995):359-368.
[4] C. Condry, “Gender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etence,”
Sex Roles11, 5/6 (1984): 485-511.
[5] 參Condry, “Gender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etence,”.
[6] G. Ramafedi, M. Resnick, R. Blum and L. Harris, “Demography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olescents,”
Pediatrics 89 (4 Pt 2) (Apr 1992):714-721.
[8] M. King and E. McDonald, “Homosexuals who are twins. A study of 46 probands,”
The Brist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 (March 1992): 407-409.
[9] K. Dawood, J. M. Bailey and N. G. Martin,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in
Handbook of Behavior Genetics, edited by Y. K. Ki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9), 269-279.
[10] P. Sprigg, and T. Dailey, eds.,
Getting It Straight: What the Research Shows about Homosexuality (Washington: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2004).
[12] W. Byne and B. Parsons, “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no.3 (March 1993):228-239.
[13] M. S. Lasco et al., “A Lake of Dimorphism of Sex or Sexual Orientation in the Human Anterior Commissure,”
Brain Research 936, issue1-2 (May 2002):95-98; W. Byne and B. Parsons,
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14] “Biological Causes of Same-Sex Attraction”
.
[15] L. Ellis et al., A Brief Report on “Sexual Orientation of Human Offspring may be Altered by Severe Maternal Stress During Pregnancy,”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5, no.1 (Feb 1988): 152-157.
[16] J. Money,
Gay, Straight, and In-Betwe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98. 轉引自“Biological Causes of Same-Sex Attraction”.
[17] D. J. Bem. “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 no.2 (April 1996): 320-335.
[18] G. Rieger and R.C. Savin-Williams, “Gender Nonconformity, Sexual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 no.3 (June 2012): 611-621.
[19] M. Siegelman, “Parental Background of Male Homosexuals and Heterosexual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 no.1 (1974):3-4.
[20] R. B. Evans, “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f Homosexual 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 no.2 (April 1969): 129-135.
[21] M. D. S. Ainsworth, “Object Relations, Dependency, and Attachment: a Theoretical Review of the Infant-mother Relationship,”
Child Development 40 (1969): 969-1025.
[22] K. Bartholomew and L.M. Horowitz,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1, no.2 (1991): 226-244.
[23] J. Nicolosi,
Reparative Therapy of Male Homosexualit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1991).
[24] L. Bieber et al.,
Homosexality: A Psychoanalytic Stud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1988).
[25] J. Dallas,
Desires in Conflict (Oregon: Harvest House, 1991).
[27] D. C. Haldeman, “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Sexual Orientation Conversion Therap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2, no.2 (1994): 221-227.
[28] 莫頓‧史強曼:《教會與同性戀——尋找中間地帶》,(香港:道聲出版社,2004),頁86-88。
[29] H. Macintosh, “Attitude and Experience of Psychoanalys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2, no. 4 (1994): 1183-1207.
[31] W. Throckmorton, “Attempts to Modify Sexual Orientation: A Review of Outcome Literature and Ethical Issues,”
Th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0, (Oct 1998): 283-304.
[33] J. Nicolosi et 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rapists who Practice Sexual Reorientation Psychotherapy,”
Psychological Reports 86, (April 2000):689–702.
[34] A. D. Byrd et al., “Clients’ Perceptions of How Reorientation Therapy and Self-Help Can Promote Changes in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02, no.1 (February 2008):3-28.
[39] Spitzer, “Can Some Gay Men and Lesbians Chang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42] S. L. Hershberger, “Gutman Scalability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Reparative Therap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2, issue 5 (Oct 2003): 440.
[43] 莫頓‧史強曼:《教會與同性戀——尋找中間地帶》,(香港:道聲出版社,2004),頁92。
[47] N. Whitehead and B. Whitehead,
My Genes Made Me Do it, revised ed (Los Angeles: Huntington House, 2010), 5.
[48] J. E. Phelan, N. Whitehead and P. M. Sutton,
What Research Shows: NARTH's Response to the APA Claims on Homosexuality, A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 (NARTH, 2009).
[49] T. Taylor and K. Ralph, “Developing Survey Questions on Sexual Identity,”
Report on National Statistics Omnibus Survey Trial 3, June 2008, Data Collection Methodology-Social Surveys.
[50] E. O. Laumann et 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1] H. H. Handsfiel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Homosexual 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1, issue 9 (Sept 1981): 989-990.
[52] R. S. Ernst and P. S. Houts, “Characteristics of Gay Persons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12, no.2 (1985):59-63.
[53] A. L. Evans et al, “Prevalence of bacterial vaginosis in lesbians and heterosexual women in a community setting,”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83, no.6 (Oct 2007): 470–475.
[54] Walt Odets,
Love in the Shadow: Being HIV-Negative in the Age of Aids (New York: Irvington, 1994).
[56] R. R. Troiden and E. Goode,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Acquisition of a Gay Ident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 issue 4 (Summer 1980):383-392.
[57] T. W. Smith, “Adult sexual behavior in 1989: Number of Partners, Frequency of Intercourse and Risk of AID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3, no.3 (1991):102-107.
[58] J.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6), 51; T. E. Schmidt.
Straight and Narrow? Compassion and Clarity in the Homosexuality Debat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110-116.
[59] J. B. Williams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Baseline Assessment of Homosexual Men with and withou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II. Standardized Clinical Assessment of Current and Lifetime Psychopatholog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 no.2 (Feb 1991):124-130; P. H. Rosenberger et al., “Psychopathology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Lifetime and Current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34, no.3 (May-June 1993): 153, table 1; 154, table 2. Rosenberger et al. 發現有45%的人過去都受過沮喪影響,並濫用藥物失調。
[60] C. Ryan and J. Bradford, “The National Lesbian Health Care Survey: An Overview,” 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sbian and Gay Male Experiences, ed L. D. Garnets and D. C. Kimm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50.
[61] M. T. Saghir and E. Robins,
Male and Female Homosexuality: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73), 274, table 14.4.
[62] 這些研究的摘要,見C. Vourakis,“Homosexuals in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in
Substance Abuse: Pharmacologic,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ed. G. Bennett et al. (New York: Wiley, 1983), 404-405; and J. M. Hall, “Lesbians and Alcohol: Patterns and Paradoxes in Medical Notions and Lesbians’ Beliefs,”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25, no. 2 (April-June 1993): 110.
[63] K. Freund et al., “Pedophilia and Heterosexuality vs Homosexuality,”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10, issue 3 (Fall 1984): 197; P. Cameron, “Homosexual Molestation of Children: Sexual Interaction of Teacher and Pupil,”
Psychological Reports 57 (1985): 27-36.
[65] Paul Cameron and Kirk Cameron,“Gay obituaries closely track officially reported deaths from AIDS,”
Psychological Reports 96, issue 3 (June 2005): 693-697.
[66] R. Herrell et al. “Sexual Orientatiion and Suicidality: A Co-Twin Control Study in Adult Men,” A
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6, no.10 (1999): 867-874.
[67] S. E. Gilman et al, “Risk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individuals reporting same-sex sexual partn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no.6 (2001): 933-939.
[69] A. King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ntal Disorder, Suicide, and Deliberate Self Harm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eople,”
BMC Psychiatry 8, no.70 (Aug 2008).
[70] A. P. Bell and M. S. Weinberg,
Homosexualities: A Study of Diversity among Men and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M. T. Saghir and E. Robins,
Male and Female Homosexuality; P. H. Rosenberger et al., “Psychopathology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Lifetime and Current Assessment,”; J. B. Williams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Baseline Assessment of Homosexual Men with and withou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C. Ryan and J. Bradford, “The National Lesbian Health Care Survey: An Overview.”
[71] J. E. Phelan, N. Whitehead and P. M. Sutton,
What Research Shows: NARTH's Response to the APA Claims on Hom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72] E, Hooker, “The Adjustment of Male Overt Homosexual,”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21, issue 1 (Mar 1957): 18-31.
[73] T. G. M. Sandfort et al., “Same-sex sex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Find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2, no.1 (Feb 2003):15–22.
[74] R. de Graaf et al. “Suicidal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a general population-based sample from the Netherland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5, no.3 (June 2006): 253–262.
[75] H. Hendin, “Suicide and homosexuality,” in
Suicide in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129-146.
[76] G. Remafedi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ttempted Suicide in Gay and Bisexual Youth,”
Pediatrics 87, no.6 (June 1991) 869–875.
[77] J. P. Paul et al., “Suicide attempts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antece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no.8 (Aug 2002):1338-1345.
[78] A. F. Jorm et al., “Sexual Orien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Results from a Community Survey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Adult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0 (May 2002): 423-427.
[81] F. Worthen, “Ministering to the Sexually Broken”, a powerpoint used in Exodus Asia Cofnerence, Restoring Sexual Wholeness: Effective Ministries to the Sexually-Broken held on Feb, in 2003.
[82] 川:〈走過同志路:一位男同性戀過來人的期望〉,《十位勇敢的兒女》,(香港:新造的人協會,2005),頁17-20。
[83] 參A. E. Sears and C. J. Osten,
The Homosexual Agenda, Exposing the Principal Threat to Religious Freedom Today ( Tennessee: B & H Publishing Group, 2003), 1-14。
[85] 請參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ICCPR第二十三條。
[86] 請參考案例:Joslin v.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No.902/1999;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Final Judgment 22 Nov 2010.